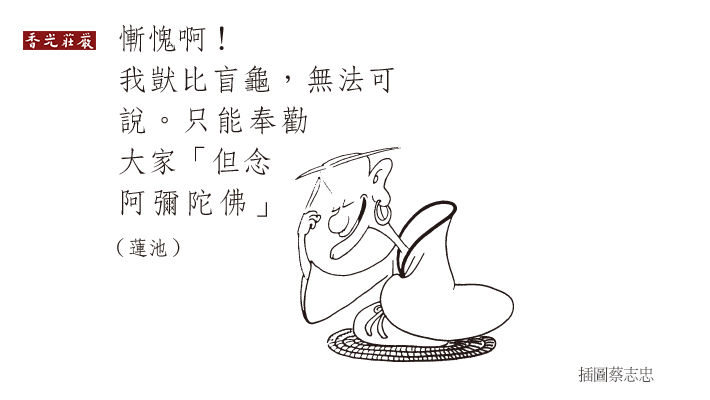
節錄自092 期
2007.12.20
釋見曄
洞澈裡邊 照見外邊/大師相對論對世局的看法
晚明時期,世局混亂。身為一個出家人,要在混亂的局勢中自處,也要關心社會、國家。不知四位大師對於當時世局的看法如何?是回應:「國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」呢?或是感嘆「國土危脆」呢?
蓮池:袾宏生不逢時,不能生於與佛同世的正法時期;曾在〈彌陀疏鈔〉提過:「袾宏末法下凡,窮陬晚學,罔通玄理,素鄙空談。畫餅何益饑腸,燕石難誣賈目。」自問尚且不能明事,哪來的智慧理論世局?
知道自己淺劣有限,對「言過其行」深感可恥,所以,我不「空談」。也曾在〈畫像自贊〉中描述自己是「瘦若枯柴,衰如落葉,獃比盲龜,拙同跛鱉。無道可尊,無法可說。」因此,也只能奉勸大家:「但念阿彌陀佛!」
憨山:蓮池老大哥,您太謙虛了!剛出家時,德清也是「只憂自己道業成就否?」
但隨著出家年月增長,也憂心百姓、社會、國家!流放到雷州時,見到當地慘況,德清曾在寫給雪浪法師的信裡提到:「值歲饑異常,米穀湧貴,民不聊生。從去秋七月,至今不雨,野無農夫,戶有盜賊,而雷陽尤甚。……今復瘴癘大作,死傷過半,道路枕藉,悲慘徹心。」
目睹雷州百姓之苦,身在中國大乘佛教,德清不禁要從「自了生死觀」擴大為「人間菩薩觀」。出世法是不離世間的!
所以,流放從軍時,曾在〈軍中吟〉自白心聲:
「……從軍原不為封侯,身經赫日如爐冶,傲骨而今鍊以柔。」「緇衣脫卻換戎裝,始信隨緣是道場;縱使炎天如烈火,難銷冰雪冷心腸。」
自己從軍的原意,本就不是為了求官祿討生活,而是將之當成修行過程裡的磨鍊。一切磨難皆作洪爐冶鐵,只求能將一身傲骨化成繞指柔。因此,常要求自己:隨緣即是道場,處處自在。
紫柏:憨山兄,您說得即是!看看我們所處的萬曆年代,並非太平盛世,而是昏君當政,吏治敗壞,黨爭滋蔓不息,賦稅繁重,民變、兵變四起的時代。
這樣一個風雨飄搖、剝削的時代,達觀不忍坐視這些貪暴無能,握著生殺大權,榨取生民血汗的君臣為所欲為,於是提出了「民為國本」的呼籲:虐殺百姓,無異於滅君。混亂的世局,身奉出世間法的佛教徒,定要挺身而出,不然世變難以終止。
當年身陷獄中時,審判官王之禎問我:「你是個出家人,留在山中修行是本分。不在深山修行,為何要到京城結交士大夫,干預公事?」達觀的回答是:「我是為了刻《方冊藏經》,修《高僧傳》,編《續傳燈錄》,還有營救憨山法師等,才來京中暫住,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戀戀紅塵。」
問:這應該就是紫柏大師您三大負欠的感慨:「老憨不歸,是我出世一大負;礦稅不止,則我救世一大負;傳燈未續,則我慧命一大負。」您關切民間疾苦,也以佛門慧命為念,這三大負欠沒有一樣是為了您自己!
至於蕅益大師,史料上很少提到您參與國家社會的運動,這一點,您的想法是什麼?
蕅益:智旭所處的年代,是萬曆廿七年(1599)至順治十二年(1655),那是十六、十七世紀交替的中國。也是不平安的時代。
政治紛擾,流賊四起,接著清兵入關,是一個改朝換代的亂世。天災、人禍相逼而來:旱災、蝗害、河堤潰決不斷,連年饑荒、兵變,處此亂世,民眾淒楚無依,流離困頓,智旭只能慨歎「孤臣無力可回天」!
雖然如此,既出家為僧,面對這樣的社會,自己也有宗教責任。但並非選擇直接入世,參與救度;而是以宗教行持來回應時代,以滿懷的悲心、同情心傾注於一切眾生。所以,我常常為國家、社會與百姓禮懺、祈願。
智旭感嘆自身障重,生不逢時,目睹時艱,「斗米幾及千錢」,而嘆民生之苦;面對「病死日以千計」,而驚訝眾生業報之深。這一切都是眾生共同所感的惡緣,共同感受的苦報。雖然佛法說這分苦報亦是幻相一場,但是,我怎能坐視這場劫難呢?
雖有滿腔熱血,但獨木難撐大局,只能藉著精勤行持的力量,來改造自己、法運及世運。竭盡己力,代眾生發願、祈求疾疫消除,刀兵偃息,風雨順時,穀物豐稔。內心祈望:百姓常享太平豐樂,不遭離苦饑荒;正法能長久住世,眾生能離苦得樂。
問:憨山大師曾以「性剛猛精進,律身至嚴。」描述紫柏大師;後世以「苦急嚴峻」形容蕅益大師。二位大師的個性或有相似之處,為什麼您們二人所選擇的方式如此不同?
蕅益:智旭曾受益於紫柏前輩,在點完前輩的文集後,後學曾心有戚戚焉寫下:「今觀其法語,精悍決裂,猶足令頑夫廉,懦夫立。柔情媚骨,不覺冰消瓦解。」前輩的剛猛之氣是向外發,直接投入濟世救民的菩薩道,如同人間的俠僧。智旭則不然,我將自己滿腔的熱情,內化於一生的宗教行持。除了虔敬發願,精勤地禮懺、持名、持咒,甚至以血書、燃臂、燃頂來表達自己虔敬發願之心。
這一生修行的色彩,願用一偈來表達:「照我忠義膽,浴我法臣魂;九死心不悔,塵劫願猶存。」
Facebo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