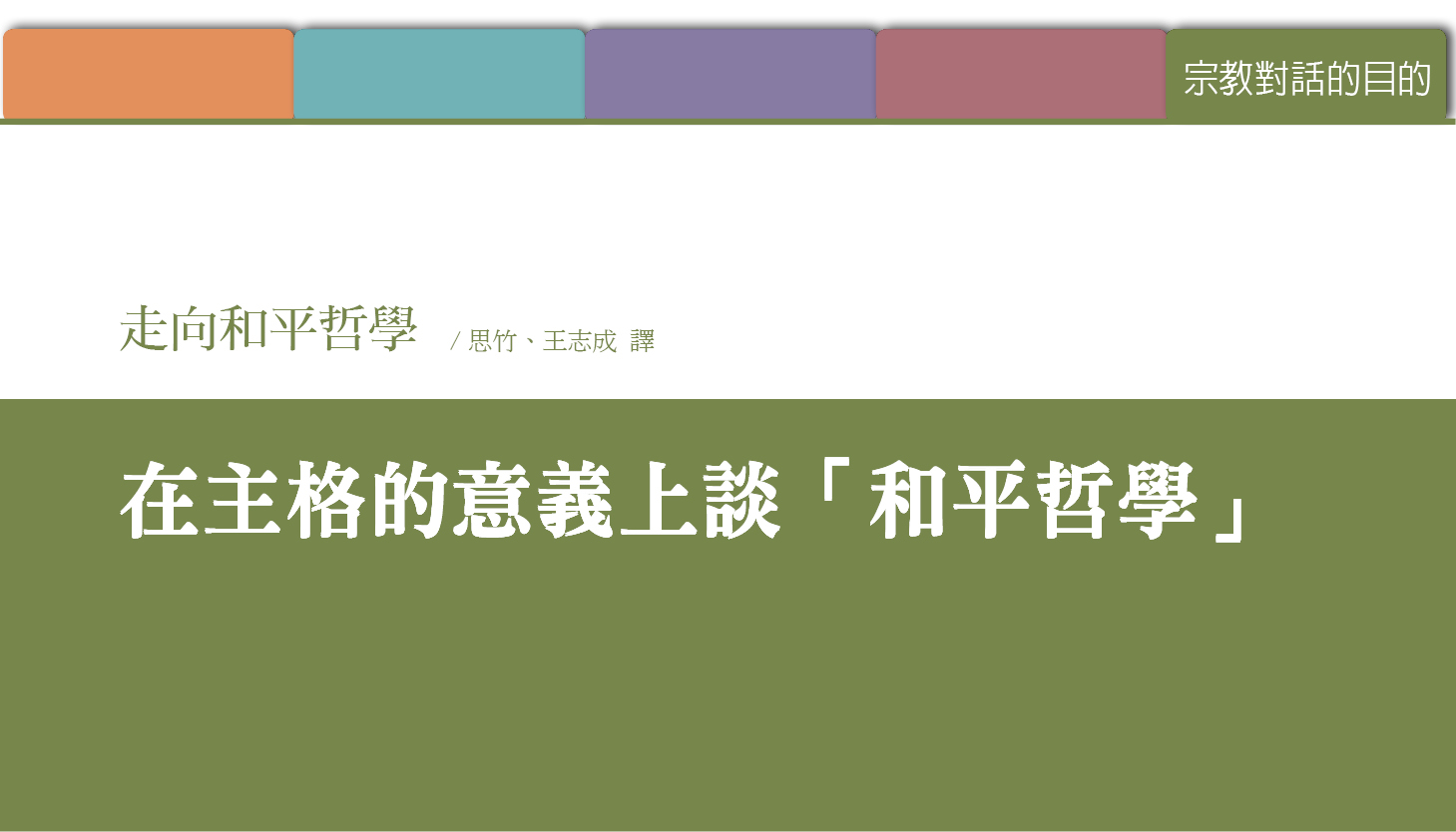
節錄自119 期
2015.06.20
思竹、王志成 譯
【宗教對話的目的】走向和平哲學在主格的意義上談 「和平哲學」
我們並不想讓「和平哲學」這一用語僅僅喚起哲學的思辨和批評的思想,它也應該試圖喚起所有真誠的哲學活動所固有的和平,也就是試圖在真正的和平中激起內在的哲學。(1)
「和平哲學」這一用語,可從主格以及賓格的意義上來理解。現在,我要在主格的意義上來談談。
「和平哲學」試圖深入理解「實在」的奧秘
宣稱創造一種來自「和平」本身的哲學,這樣做無異於違抗現代西方哲學思潮。人們習慣於把哲學視為對真理的理性探求——儘管理性常常只不過是在追求明晰性。
然而,在世界其他地方,我們發現了一個更真實的哲學觀念,這個觀念在西方歷史傳統中並非鮮為人知。權威人士如傑出的西塞羅(Marcus Tullius Cicero)[2] 把哲學描述成「靈魂的文化」(cultura animi),亦即生命、精神、心靈或靈魂的文化。只要我們的靈魂得到充分的培養,精神得到和諧的培育,「和平哲學」就會出現——這不只是和平的哲學,它也反映了「實在」的和諧,同時也促進了「實在」的和諧,它自然成為和平的原因與結果。它之所以是「和平」的原因,是因為它增進或重建宇宙的和諧;它之所以是「和平」的結果,是因為它產生於一種平靜、和平的精神。
這種哲學尤其具有真實性。它是一種理智活動,它試圖盡其所能地深入理解「實在」的奧秘。這是一種存在觀,是於「存在」的生命中有意識的參與。若與被認識的事物沒有共性,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認識。因而,「和平哲學」預設了「實在」終極結構的和諧性。
這種假設是一種嚴格的同義反復,而不是任何別的事物。由於我們自己內在的要求,我們不得不認為宇宙的終極結構是「和諧」的。我們怎麼可能斷言「實在」不是和諧的——「實在」與它應成為的事物是相異的呢?正因如此,我們必須擁有一個內在於「實在」本身的、能隨我們支配的模式,這個模式允許我們設定「應該是」(oughting to be)之超然性。
但事實上,並無這種模式,我們除了「實在」本身,再也沒有別的標準了。歸根結柢,只有「實在」才能讓我們度量、思考、判斷它是「什麼」。那些必須「是」的事物都從屬於「是」的事物,這個「是」(is)與「存在」(being)同義,即指「生成」(becoming) 和「『應該』是」(“oughting” to be)。因此,「和平哲學」不只是被動的觀察,也是主動的參與。
「默觀」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無比的和諧
又是西塞羅通俗化並發展了「默觀」這一觀念。我在他處已論述,「默觀」不僅僅是「theōria」;當然,「theōria」也不僅僅指該詞現代流行的含義——理論(theory)。「默觀」既是理論又是實踐,既是理智的活動又是行動的參與。偉大的上師馬爾巴(Marpa)[3] 告訴他的弟子、十二世紀無與倫比的西藏聖人密勒日巴(Milarepa)[4]:「無間斷地禪修和行動是最好的療法。」真正的默觀者是兼具思考和行動的人。「默觀」是理論和實踐的整合,說得更確切些,它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無比的和諧——儘管它們之間一旦發生分裂,只有新的純真(new innocence)才能再次完成這一整合。這就是我所指的「和平哲學」。
讓我們換個說法。甚至古代基督教學者都懷疑,如果不生活在上帝恩典中,怎麼可能培養一種真正的哲學。古代印度的學者也斷言,如果沒有一種超然的、和平的精神,人就不能達到真理。真理即解脫,對於這一點,現代西方文化的反應是:人可以是個偉大的數學家,同時在道德上又是一個墮落之徒。我的反對理由是,在最深層、最傳統意義上理解的數學,情況並非如此。我們如果僅僅把數學理解為算術,是電腦可處理(並肯定比我們更快、更正確)的學問,那就對了。但除非我們的整個「存在」投入其中,否則思想或任何包含我們人類整體的活動(例如美學活動),就不可能是真實的。倘若我們在生存中處於撕裂的狀態,我們的「存在」就不可能整個地投入。換句話說,除非我們的「存在」是整體的,否則思想就是不真實的。
現代社會如此動盪不寧,其中有個原因是:為了達到和平的哲學而鬥爭(但這並非前述的「和平哲學」),我們於是強加自己「和平」的概念。然而,任何可從人的精神中產生但與自身及世界不和諧的哲學,都不可以稱為「哲學」[5],更談不上「和平哲學」了。維根斯坦(Ludwig Wittgenstein)[6] 在《哲學研究》(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)中明確地寫道:「真正的發現是這樣的事物:當我不想從事哲學時,它也允許我這樣做,它可以給予哲學和平。」因此,儘管他是「現代性之子」,他也能接受「哲學只不過是論證的問題」這樣的觀念。但在後笛卡兒哲學的世界,這仍然是一個狹隘的哲學觀念。
總之,「和平哲學」這一用語包含了哲學觀念本身的綱領,也包含了對哲學觀念本身的挑戰(進一步說,還包含和平的性質)。萬物相互關聯,佛教傳統說「緣起」(Pratītyasamutpāda),崇拜濕婆的印度教傳統說「凡事彼此關聯」(sarvam-sarvātmakan),基督教傳統則說「上帝是一切之中的一切」(panta en pāsin)。
(1) 為原注;[1] 為譯注
(1) 一九八九年,米格爾.西格恩(Miguel Siguán)編輯了《和平哲學:向雷蒙.潘尼卡致敬》(Philosophia pacis: homenaje a Raimon Panikkar )一書向我致敬,我為了表示感謝作了回應,本章即是主要取自我的回應。儘管某些要點都已論述或再次被提到,但我覺得這概括性的介紹有助於對「和平哲學」作一概觀。
[2] 馬庫斯. 圖利烏斯. 西塞羅(Marcus Tullius Cicero,西元前106-43 年):羅馬共和國晚期的哲學家、政治家、律師、作家、雄辯家。他精通修辭學,並熟知當時流傳的伊比鳩魯(Epicurus)與斯多噶(Stoics)學派哲學思想。他也是拉丁文學的大家,十六世紀以後,學者們學習拉丁文,莫不以西塞羅的文體馬首是瞻,因而教育史上有「西塞羅主義」(Ciceronianism)的出現。
[3] 馬爾巴(Marpa, 1012-1097):西藏的大上師與大譯師,也是密勒日巴的根本上師。他自印度帶回並翻譯了許多密續,這些教法經由密勒日巴與其他弟子傳下,形成噶舉派的基礎教法。
[4] 密勒日巴(Milarepa, 1040-1123)西藏偉大的瑜伽士與詩人,馬爾巴的最主要弟子,也是噶舉派的創始者。他在修道上所遇到之考驗與艱辛的故事,以及傳神生動的道歌,都是藏傳佛教中最受大眾喜愛的作品。
[5] 潘尼卡把「哲學」理解為「解脫之知」、「愛的智慧」,人們通常把哲學理解為「愛(追求)智慧」。其實,近代哲學以來的哲學主流並非「愛智慧」,而是「愛知識」。潘尼卡告訴我們哲學的根是「愛」,哲學的枝葉是「智慧」。
[6] 路德維希. 維根斯坦(LudwigWittgenstein, 1889-1951):生於奧地利,是分析哲學及其語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,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,其研究領域主要在數學哲學、精神哲學和語言哲學等方面。著有《邏輯哲學論》(Tractatus Logico-philosophicus )、《哲學研究》(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)等書。
Facebo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