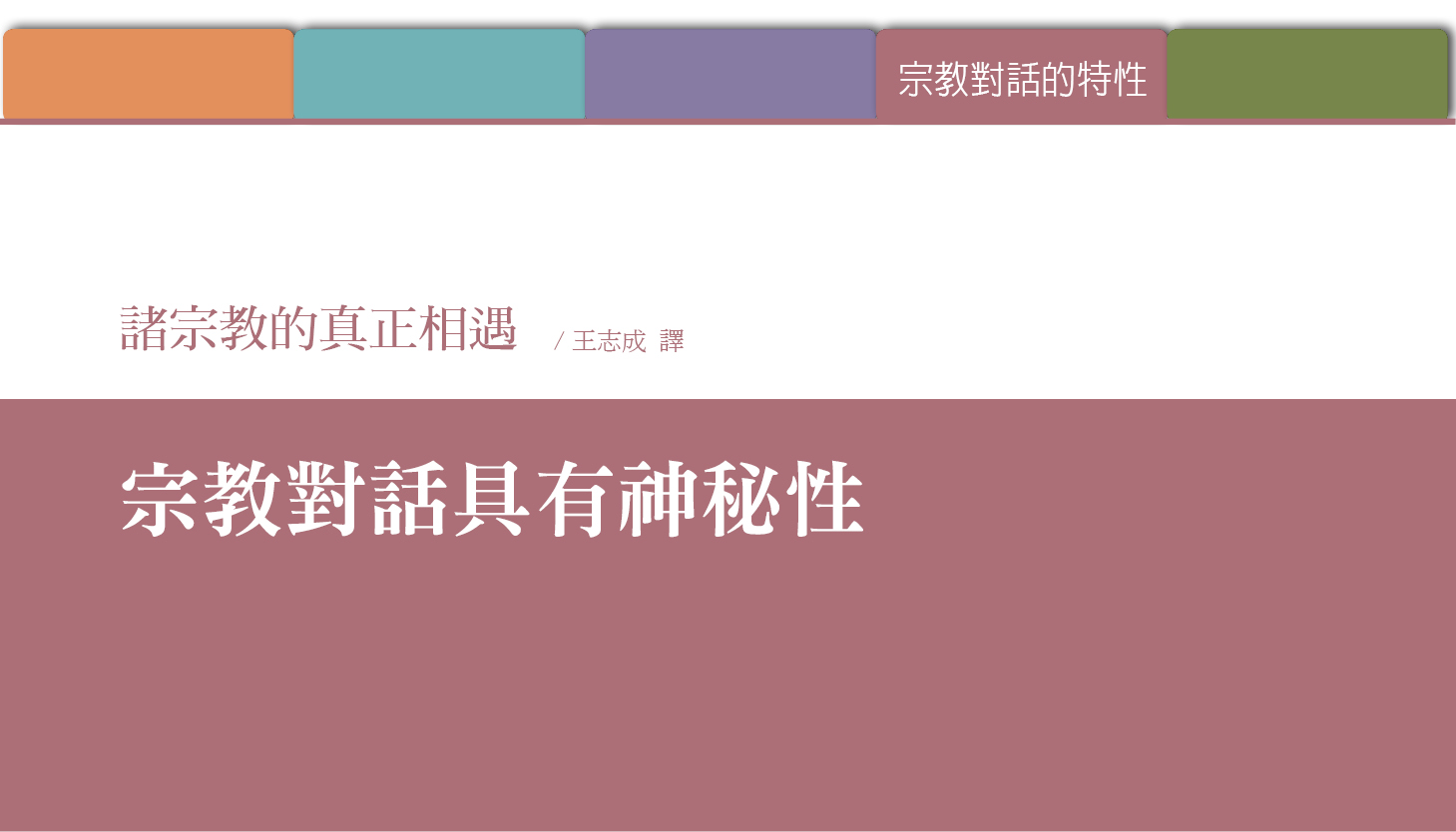
節錄自119 期
2015.06.20
王志成 譯
【宗教對話的特性】諸宗教的真正相遇特性六:宗教對話具有神秘性
「對─話」(dia-logos)不僅意味著通過「邏各斯」繼續推進,以及獨自處理「邏各斯」,而且意味著突破「邏各斯」——越過「邏各斯」(dia ton logon),而進入神話(the mythos)。所謂「啟蒙運動」最軟弱的支柱,或許就是這一幼稚的信念:原則上一切事物都可以通過人或神的理性而獲得澄清。從笛卡兒、康德到布特曼(R. K. Bultmann)[34] 和現代自然科學,都主張啟蒙運動的這一信念。許多人依然夢想著普遍數學(mathesis universalis),主張以數學語言把握「實在」的理論之可能,似乎「實在」可以通過超級電腦來了解。
理性是人的批判力量,它讓我們擁有自我意識,但康德則以無意識地自我辯護的方式來談論「純粹」理性,首先它是那樣地純粹,以至於使它處於批評之外或批評之上。(35) 理性從一開始就被設定,它代表神話的格式塔(Gestalt)[36]。人們總是會遺忘或忽視自己的神話,畢竟神話和「邏各斯」是一起的。宗教對話如果真有活力,那麼,它就不能在對話之外留下神話。(37)
這一過程可以強調三個方面:
(一)對話突破「邏各斯」,並讓神話開放;
(二)宗教對話的各方,力求參與進它們各自所信的內容之中;
(三)在同一神話中,分享所設定的對話界限。
對話突破「邏各斯」,並讓神話開放
概念是重要的,甚至是必要的,但概念從來並不足以帶來民族之間或宗教傳統之間整體的相遇,概念的對話依然只是辯證法。對話的對話不只是(不少於)爭論或理性討論,在對話的對話中,我們意識到自己所使用的概念產生於更深的源泉,我不僅讓其他人知道我,而且通過對話夥伴的批評和揭露,我開始更好好地認識自己的神話。
對話的對話不是為了在觀念的競賽中獲得勝利,也不是為了超越實際的意見差異而達成一致。相反地,通過對話,夥伴的每一方加深他(她)自己的領域,以及為尚未理解者開啟可能的空間,對話的對話即是試圖共同擴展理解領域。這不是恥辱(對笛卡兒來說曾經是的),因為對話各方並沒有將各自的立場絕對化。
每一個宗教都活出它自己的神話。這神話是個「大熔爐」,「邏各斯」就是從這個「大熔爐」中冒出來,並凝結在概念的結構和教義之中。將這一「邏各斯」作為出發點並不是一種邏輯前提,相反地,它加強了不言而喻的前設,這些前設形成了每個傳統的理解視域。與此對應,傳統的觀念於是被視為具有了意義。
宗教對話若不考慮這一視域的不同,就會陷入誤解之中,而且絕不會達到每個傳統都接受其自我理解的基礎。這裡所蘊涵的意思是,宗教的相遇不可能被化約成教義的比較。每個宗教就有如星系,自發地形成它自己的思維標準,以及它自己關於「實在」和真理的標準。所以,為了引出有效的比較,人們必須逐漸認識到我所稱的「形式相似的等價詞」(homeomorphic equivalent)。(38)
嚴格地說,可以沒有比較宗教學,甚至可以沒有比較哲學,(39)也沒有中立的(「非宗教」[a-religious]或「非哲學」[a-philosophical])立場,(40) 所有的這些讓我們向神話開放。但是,在這一意義上,神話是不能加以比較的,它們在字面上不可比較。它們是讓每一種比較成為可能者,它們提供視域,任何比較都必須在這視域中進行。當然,概念和教義是可以比較的,但這種比較只能在先前被接受的立場之背景下進行。
這就是不直接針對學術或教義目的的相遇之所以會如此重要的原因。共修(satsangs)、節慶、共餐、各種聚會、為共同項目合作和貢獻、社交中的殷勤和最淳樸的行為等等,其實常常表明了最重要且最有力量的對話事例。
宗教對話的各方,
力求參與進它們各自所信的內容之中
無論宗教生活是否展示在清楚闡明的教條、普遍的洞見、被解釋的經驗、被履行的儀式或被運用的象徵之中,它都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語詞——信念(belief)——來加以概括。宗教是一種信念問題,信念是包羅萬象的神話,它使得各種構成宗教的展示成為可能。事實上,我們可以把這種宗教的神話,視為是默許有關任何既定事態之可能性(因而也是可信性)狀況的集合體。因此,宗教對話必須是信念的對話。為了理解宗教,你必須知道它的信念。對話即源起於信念且和信念有關,但是,這樣的一種對話將如何維持?人可以理解信念的陳述,而無須參與信念嗎?
在胡塞爾(Husserl)[41] 現象學的激勵下(這種現象學把「意向物」[the noêma]視為純粹的直觀內容),我斗膽引進「pisteuma」([信徒]所信內容)的概念。透過思考的行動(noêsis),我們思考(noein)思想(noêma),於是我們獲得作為意識的純粹意向性內容的意向物。但是,意向物並不允許我們將任何客觀真理或生存現實歸於它自身。與之平行的是,信念也確實是自成一類的覺知,它們指向信徒所信的內容。但是,信徒所信的內容向外人呈現時,是不為外在觀察者所共用的意向物。
換言之,非信徒能夠認識到信徒所說的內容(例如,「多羅[Tārā]是應該受到崇拜的女神」),但是他們不可能理解,就不能履行那種信念。也就是說,在多羅女神那裡,非信徒無法理解信徒的所信內容。如果真能認識到什麼的話,他(她)就會獲得某種不同於信徒所信內容的意向物。所以,我是透過自己的意向物而接受了他的所信內容,如果一個人不能共用所信內容,他就不能有意義地談論它;人所能描述的就是他自己的意識內容——意向物,但並非信徒的所信內容。
信徒所信的不是一種理性的、可冥想的意向物(這種意向物可[通過外人的理解力]傳達),而是信徒自己所信的內容。如果我不進入這一所信的內容,就不能描述信徒所信的內容,而只能從我自己的觀點描述我假定信徒所持有為真的事物。但是,如果我不相信信徒所相信的內容,那麼,就無法到達所信內容的本身。
這應該意味著每一種信念的財富(thesaurum fidei),就如某些宗教自己所表達的,將保持無媒介並且讓人無法理解嗎?完全不是!我的意思只是說,如果沒有對話,道路就會被堵塞。為了獲得他人的所信內容,我必須以某種方式堅持他人所信內容是真實的,亦即我也需要相信其他人所相信的內容。換言之,信徒的信念本質上屬於信徒所信的內容。如果我不參與這一信念,我們就是從兩個不相融的平台上交叉地談論目的,例如,我的表達和他人的信念;我的意向物和他人所信的內容。總之,宗教現象學的意向物,實際上都是信徒所信的內容。
我所要說的是,如果我確實要與他(她)相遇,我就必須以某種方式參與夥伴的信念。所謂的「以某種方式」即是指我必須進入他(她)的神話。(42) 對話是一種走向新的、真正之宗教現象學的方式,唯有如此,我們才能澄清許多一直困惑著宗教史的誤解。對話不僅能引生宗教的寬容,而且能為宗教帶來全新的解釋。
在此,信仰和信念之間的區分變得極為重要。信念將自身表達在陳述之中,而信仰將自身展示在生活中;信仰是人的一個構成性維度,而信念是信仰的特定運算式。在這一意義上,人們可以誠實地將他們的信仰表達在不同的信念陳述之中,而這一事實只是不同文化和宗教的自然展示。
在同一神話中,分享所設定的對話界限
我們不可能總是能與另一方進行真正的、有深度的對話。對話夥伴的各方必須分享同一神話,或至少部分地處於同一理解的視域之下。當然,這一共同的神話必須在「相遇」本身中慢慢地湧現。但是,只要它未被分享,就不可能有宗教間的溝通。
例如,只要人們在他們的感知領域內發現一棵樹,那麼,一棵樹總是一棵樹,人們不會對之產生深度的理解。對那個人來說,這棵樹僅僅只是植物電腦;但對另一個人來說,它是居住著「靈」的一個身體。如果他們說,他們無法理解彼此,那麼,他們就如同某個人非難另一個人「說廢話」,或某個人將另一個人納入他自己的範疇。當然,這已經接近於溝通。當他們意識到並不理解彼此,並再次嘗試找到可能理解的基礎時,這就是一堂對話課了。雖然絕不會保證成功,但「嘗試」本身就是對話。
現代性產生了文化間的神話。例如,人性、民主、和平和世俗性等都是神話,它們都具有一定宗教間的合理性。只有分享到這樣的神話,我們才確實能夠彼此溝通。
另一方面,一個共同的神話更加易於精確地區分教義。例如,相鄰的宗教常常發展出相抗的態度,儘管他們在神話層面具有相似性,但要讓他們彼此間進行對話,卻可能特別困難;而有時它對相距較遠的宗教則更容易理解一些,因為在那遠處的宗教中已經培養了某種相互的同情。舉個簡單的例子,基督徒和猶太教徒之間的許多信念,儘管都具有基本的相似性,但是兩者還是常常成為相互厭惡的犧牲品。
[34] 布特曼(R. K. Bultmann, 1884-1976): 生於德國, 曾先後在圖賓根(Tubingen)、柏林和馬爾堡(Marburg)學習神學。一九二一年以後,長期擔任馬爾堡大學教授。著有《信仰和理解》、《作為古典宗教的原始基督教》等書。
(35) 參見M. Tanabe, Philosophy as Metanoetics , Berkeley, U. C. Press, 1986。其中具有深遠影響的批評:「就純粹理性的批判而言,理性作為批判主體總是留在安全區,在那裡維持它自身的安全,無須對批判本身進行批判。正確地說,因為理性不能因此避免自我破壞,從事批判的理性和被批判的理性必然不能彼此分離……理性必須承認它缺乏批判能力;否則,批判的理性只能不同於被批判的理性。無論如何,理性都難以避免自我破壞。換言之,試圖通過自我批評而建立它自身資格的理性,最後必定和它自身意圖相反,承認它自身絕對的自我破壞。」(頁43)
[36] 格式塔(Gestalt):意譯為「模式」、「形狀」、「形式」等,意指「動態的整體(dynamic wholes)」。格式塔學派主張人腦的運作原理是整體的,「整體不同於其部件的總和」。例如,我們對花的感知,除感官資訊外,還包括對花過去的經驗和印象,而形成對花的感知「格式塔」。在心理學中,此詞表示任何一種被分離的整體。格式塔也被譯為「完形心理學」。
(37) R. Panikkar, Myth, Faith and Hermeneutics , New York (Paulist) 1979; “Mythos und Logos. Mythologische und rationale Weltsichten,” in M. P. Dürr/ W. Zimmerli (eds.), Geist und Natur , Bern (Scherz), 1989, pp. 206-220.
(38) 我把「形式相似的等價詞」(homeomorphic equivalent) 理解為第三程度的類比, 它揭開了各自體系中相應的功能。參見The
Intrareligious Dialogue , New York(Paulist) 2, 1999, p. 18 ff。
(39) R. Panikkar, “What is Comparative Religion Comparing?” in G. J. Larson/ E. Deutsch (eds.), Interpreting Across Boundaries. New Essays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, Princeton (University Press) 1988, 116-136.
(40) R. Panikkar, “Aporias in the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Religion,” in Man and World , Nr. 13, 34, pp. 357- 383.
[41] 胡塞爾(Husserl, 1859-1938):德國哲學家, 現象學創始人。著有:《算術哲學》(Philosophy of Arithmetic )、《邏輯研究》(Logical Investigations )、《純粹現象學通論》(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)等書。
(42) R. Panikkar, “Verstehen als Überseugtsein,” in H. G. Gadamer/P. Vogler (eds.), Neue Anthropologie , Nr. 7,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, Teil 2, Stuttgart (Thieme) 1975, pp. 132-167.
Facebook